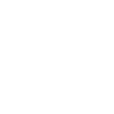在休谟看来“如果没有正义,社会必然立即解体,而每一个人都会陷于野蛮和孤立的状态”,好在电影《三大队》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正义的光辉,某种程度上,其也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德性追问中,叩问普通个体生命的责任与担当。进一步而言,《三大队》绝不仅仅拘泥于塑造公安局刑侦“三大队”中人物命运颠沛流离的群像,更重要的在于,电影自始至终诠释了对微观个体正义与公道的问询与守望,在此种意义上,显然也抛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哲学议题,即电影的意旨内涵——“何种正义,谁之责任?”
正义何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柏拉图的“正义观念”进一步发展、完善后,确证了正义作为个体美德而存在的价值。可见,所谓正义应当首先来自个体之善的坚守,或者说,对善之理念的某种具象化实践,即葆有能够凭借自身之力捍卫善的义务。因此,正义先行为“应然”层面的体认,来自个体对社会生产实践本应当具备的道德准则的阐释。质言之,人之生命主体有维护正义的必然要求。在这种审视之下,《三大队》中张译饰演的主人公程兵从开始作为警察时的职责所在,逐渐演化为追凶十余年拼尽全力的正义化身,本质上就是一种个体对善的执着。当然,这种基于“善”的“我执”,在佛家里谓之以“我执为根,生诸烦恼;若不执我,无烦恼故”,不难看出,从风光一时的三大队队长到阶下囚,再至出狱后的普通人身份,程兵骨子里贯穿着一个人民警察内心颠扑不破的正义执念。正如卡尔·弗里德里希所说,“正义的理念(eidos)是一种超验的存在,不能用感觉来证明其存在”。因此,程兵内在涂抹着为正义而拼尽全力的人生底色,并将其视为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道德标准和心中律令。这也使得横跨七省,万里追凶,只为寻找真相这一过程变得可信可感。
实际上,正义除却个体善的存证之外,还表现为一种群体的善念,即“共同体的善”(the good of community),也就是群体之间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一言以蔽之,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是一种“至善”,也可称之为最大的正义。无论是罗尔斯的“共同体观”,亦或是桑德尔的“构成型共同体观念”,皆指向了社会有序发展不可遗忘的共同体之善。在这个层面上,不得不说陈思诚团队将这篇千余字的非虚构故事《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点石成金。故事中王大勇在审讯中意外死亡,三大队人员锒铛入狱,成为阶下之囚。确切地说,三大队里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家庭破碎、未来不存,自我意义消亡的现实命题,但好在电影赋予了三大队这个曾经所向披靡的英雄团队在跌落谷底后依旧高呼“为心中正义与公道奔走不息”的形象。“天人迭胜谁能测,祸福无常不待评”,换作一般人,遭受牢狱之灾后,或将再难伸展一腔热血,但工程兵以及背后的三大队恰恰是最为有力的证明。可见,三大队的群体之善最终得以转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共同体的善。在这个维度上,正义已经成为个体与群体必然捍卫的道德秩序,毕竟,一俟正义共同体之善不存,更难以维系整体的社会公平。
由此,若想使得社会正义共同体之善在更大意义上成为人们良善生活的保证,便需要牢牢固守“道德责任”的理念。这便是程兵这一人物角色为何如此之真实,从而深深触动观众内心的关键点。无论是三大队的队长身份,亦或是出狱后的普通人,程兵本质上是妻子的丈夫、女儿的父亲,但却在时间无垠的道德荒野中,愿意高举责任的火把,捍卫自己头顶的正义星空与内在的道德律令。因此,像程兵一样的三大队成员,以他们的偏执与热血,诚恳与担当,捍卫与笃定绘就了一幅葆有凡人微光的人间道德图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程兵倾尽所有,无欲无求,历经崎岖坎坷的十二载万里追凶路,只为将凶手绳之以法的信念究竟因何?私以为对“道德责任”的贯彻已经成为人物身份难以涂抹的亮色。何为道德责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行为相对于我们的中道,是一种决定着对情感和行为的选择的品质,它受理性的规定,像一个明智人那样提出要求”,也就是说,只要当人们可以按照自我意愿去实践,且作为行动主体的行为人能够知晓自身行为及其由此所产生的后果时,主体行为人才能够饱受相对应的道德赞誉或批评。质言之,人之主体须葆有良好的德性,才能够使之更好地对自身行为负责,也即道德责任。如此,就不难看出程兵的坚守已然成为一种内在的信念,其身体中流淌着一种更为理性与通达的血液,而受害者家属的一句“好警察”也道出了程兵心中的真正答案,所以,道德责任不仅是程兵职业属性的天职,更是其作为社会群体之中个人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三大队”本就是一个充满“道德责任”命题的隐喻符号,既指向了个体责任的秉持,又延展至社会层面上的责任秉持。
毫无疑问,正义是一切德性的总括,亦是社会常态化运转的不二法门。一如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所言,“正义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这也确证了程兵及三大队为何万里追凶的缘由。诚然,正义绝不单单是个体的行为与群体的口号,理应诉诸于实实在在的道德良知与责任实践,如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抵达个体自我与群体社会的良善生活。(作者:韩贵东)
 长三角微电影网
长三角微电影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