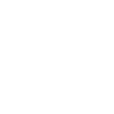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具体阐明了人之主体为之终身奋斗的道德目的,即抵达道德“至善”,这层对于德性如何作为“至上之善”的认知,为人们获得良好生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个体在生活之中道德善的获得往往具有局限性。毕竟,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体验常呈现为一种“正向”相关性,而影像作为假定性认知的道德源泉,本身就充满多重可能。在这层意义上,犯罪悬疑类型片充当了伦理道德阐述的关键媒介。其以道德伦理困境场的预设为观众建构起了个体、家庭亦或社会层面的道德关系。《第八个嫌疑人》作为现实事件改编的犯罪类型电影,为观众钩织了错综复杂的伦理道德网。诚然,在某种意义上,其填补了国产犯罪类型片的市场空白,但似乎并未抵达个体之道德善的美好愿景,更无从说起道德至善的获得。
倘若要实现影像道德善宣扬的意义必然需要塑造立体、丰满、典型化的人物形象,而不是单薄、干瘪、乏力而又无关痛痒的“纸片人”。概言之,犯罪类型片首先要关注的是何者作为行动个体,产生怎样的伦理道德选择?这才是人物充满张力化表达的前提,且这种考量不应当被悬置于故事之外,也不能够丧失具象化的行为动机。然而,在电影中,观众看到更多的是早已按照现实故事,即95年全国十大案件之一的“12·22番禺抢劫运钞车案”截取而改编的剧本。以至于电影中的人物似乎脱离了现实案件中“人之为人”的这层意义,即便大鹏、张颂文、林家栋、孙阳等演员的演技可圈可点,但问题在于他们所饰演的悍匪陈信文、警察何蓝、王守月、胞弟陈欣年等似乎从一开始便丧失了个体的行为动机,给人一种处处有疑问的观影体验。何蓝的出场沦为“打酱油”的角色,陈信文工程失意后的抢劫谋划,王守月因交通喧嚣误入打劫商议现场,陈欣年数十载在养老院过着轮椅上的生活等等,影片中有太多交代不清,厘定难晰的人物铺陈,却唯独丧失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应该拥有的基本道德好恶观。比起还原人物的善,电影中最难的莫过于如何呈现人物之恶,以及为何朝向恶。当然,每个人物都具有多面性,越是塑造典型化的人物,更应当刻画出人物变化前后的逻辑关系、因果设定。只是,电影仅仅顾及了跷跷板的一端,忽略并摒弃了对人物另一端的描摹与交代。
此外,道德善的谋求与寻觅并非个体独自成长的结果,其需要家庭作为基本的度量单位,也就是以家庭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的伦理关怀。可以说,家庭伦理关系的好与坏构成了人物面对欲望与理性选择的一个关键权衡要素。翻开中国电影史册,其中向来不缺少家庭伦理道德阐释的佳作,如吴贻弓《城南旧事》,杨德昌《一一》,沈浮《万家灯火》,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这些围绕家庭伦理而出发的电影或多或少都为观众印证了一个基本观点,即家是作为个体冷冷清清与风风火火生命各异旅程的重要羁绊。反观电影,对于每个人物的家庭关系的伦理叙事不仅有所缺席,且并未直接性地影响故事中的人物遭遇。即便,电影以大量的镜头强调了大鹏所饰演的主人公陈信文背后的家庭情节,但陈父的言行举止透露着一种疏离感,其与林家栋饰演的警察王守月的几次对谈并未让观众产生浓厚的家观念。隐姓埋名后的莫志强在新婚大喜之日拨通其父电话,一言未发的隐忍与克制也宣告了家庭伦理关系的破碎。试问在特定的年代背景下,什么样的际遇会造就陈信文对父亲心中有愧而膝下无言的表现?如果,陈信文有意逃避,可以做到新婚之日也只是将爱沉默地诉诸远方,那故事的终章其父又怎能因为王守月多年如一日的到访而放下内心的戒备。前前后后的情节中,有太多远离“家”的疑问,两位陈氏兄弟也存有诸多与家渐行渐远的行为选择,乃至于将本就碎片化的人物印象拉向了对立面。常言道“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毫无疑问,家庭与童年生活不可分割,甚至是孕育童年喜怒哀乐的关键港湾。因此,如果丢掉家庭的伦理空间,便无法朝向道德善的终点。
当然,《第八个嫌疑人》也有其道德善的光亮之处,只不过,零星的人性微光太过短暂而又显得力不从心。缘何有这种喟叹?电影《第八个嫌疑人》意在表达“第八个”这层量化的悬念意旨,也就是除去七人之外的“第八个”。众多映后声音认为,电影与前期自媒体宣传不符,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标题党嫌疑,第八个根本无从具象化谈起。但笔者以为,我们人人都有可能是“第八个”,这恰是导演李子俊的有意说明。面对恶善的选择,我们都有可能是第八个嫌疑人。或许,只有第八个嫌疑人才有可能被人慢慢忽略,才会假借时间的推移湮灭自我内心的恶之花。在这一点上,电影确实有对人性深处“见微光”的憧憬与期待,这也导致了莫志强在穷途末路之际,再次面临人性道德考验时,为留住眼前之爱与当下利益,只能选择毁灭残存的人性,转而做出让其弟陈欣年“消失”的举动。有趣的是,导演在此时巧妙地安排了一段盛大烟火的情节,仿佛“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人性敲打与叩问,善恶的选择当然也如这刺破黑夜苍穹的烟火一般,转瞬即逝。功名利禄,是非成败,皆在回望时,已空空如也。正因此,电影的结尾处如此富有意料中的转折性,莫志强还是未能回到陈信文当初的恶。在此时,电影赋予了人物内心深处踟蹰游移而又微弱的善。只是免不了唏嘘不已,不知这份善是主动选择,还是顾及家人后的被动与无可奈何。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实际上,道德善并非置于高处的理念,在获得善的路途中,亟待朝向苦难,踏实地行走。“善的意志”也不以一切外在物欲为条件,在谋求幸福的过程之中,如何成为“人”才是最为重要的着眼点。电影最大的魅力正在于为观众提供了思考善恶的契机与空间,《第八个嫌疑人》还需要还观众一个更为具体的“人”之道德善恶观,“人”之伦理的良善选择,如此,才可以获得电影内外有关“人之初”的思索意义。(作者:韩贵东,系中国科幻研究中心“起航学者”,哲学博士)
 长三角微电影网
长三角微电影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