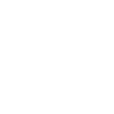阎肃
1993年我经常“边采边写”。
1月,采访了作曲家雷蕾。她先声明自己从小是打着都不肯学音乐的,而是爱跳舞。至于学音乐是因为到了恢复高考的时候理工科或是文科都没什么优势,只好走老爸雷振邦先生的路学音乐。对于自己的作品她也不像其他人那样评价:
我自己都不大满意,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就喜欢了。就连《渴望》里的“悠悠岁月”我也觉得挺没劲的,挺一般……这是跟你实话实说。反正我是在认真地写,可是我这人一直就不自信。
雷蕾是极少的对自己评价这么低的作曲家。之后,我4月在《中华家教》杂志上发表了《雷振邦的掌上花蕾》。
这一年的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上,那英演唱了一首《雾里看花》,很受欢迎。
我年前曾经采访过阎肃先生,在《中国时代》杂志1993年第3期上刚发表了《蜂酿百花蜜 香甜在人间——阎肃先生印象记》,于是向阎老打听一下创作始末。原来导演是要求他写一首“打假歌”,他琢磨那时假冒商品最多的是化肥、农药等,总不能写“化肥是假的,农药是假的”吧?思来想去,不能太直白,要朦胧一点,将那些假的、差的、坑骗顾客的东西虚化成一个“纷扰”的世界,需要认真识别。他由此联想到川剧《白蛇传》中的“慧眼”,灵感一闪,于是“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把这纷扰看个清楚……”而作曲者孙川采用词曲节奏倒错的写法也很有特点。我为此写了一篇评论:《<雾里看花>的朦胧美》
春节后,作曲家冯世全找我:“咱们一块去趟广州吧,参加他们电视台系统的新歌评奖。”
去了广州,发现我们这些外来客基本上就是个摆设。人家已经评完,无非叫我们画个圈圈,这样可以告诉被评的作者和歌手评委阵容是公平的。
不过我听到两盘磁带觉得不错,一盘陈明的《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另一盘高林生的《牵挂你的人是我》,却是没有任何奖项。
我对冯世全说起这个事,他和其他几位评委也有同感。但对主办方一说,他们委婉地表示已经定了,结果无法改变。
我愤愤地说:“他们可以想个办法嘛,设个新人奖之类的,别以为我们的耳朵都是吃素的。”
冯世全又去说了。他们还真给了面子,给了陈明和高林生“新人奖”。
意识到这些已经是在签约制下出现的新人,我写了一篇《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大概概括了当时的歌坛景象。
大约同时,也在采访那英的基础上在《中华儿女》的第三期上发表了《那英、那歌、那人》。当然最大感慨就是这个中学时代一天到晚打架闹事的“问题少女”,和齐秦一样都有一个走向音乐之路的引路或支持者的姐姐。
3月,采访了上世纪80年代北京两个重量级的音乐编辑——吴海岗和朱一公。他们很详尽地给我讲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新生唱片产业的发展故事。比如,朱一公告诉我近年来大火的《我和我的祖国》,是他在1984年的时候参与录制的。在“中录”(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录李谷一另一盘《我和我的祖国》,秦咏诚作曲。李黎夫是他的学生,当时还在沈阳音乐学院上学。秦咏诚当了院长了,李黎夫来给他配器做这盘带子。
3月31日,采访了黑子——王彦军。作为当年“音像界最年轻的总经理”,给我讲述了音像业上世纪80年代大发展时期的各种景象,以及他亲身参与的一系列原创活动,包括早期内地和港台音像界的交流合作的往事。
此间也采访了从日本归来的苏越。最深的印象是他说在日本打工初期,能听到的音乐只有半夜往家走从居酒屋里传来的音乐。
4月,采访了田震。她告诉我名字怎么来的:“是我爹从‘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里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不过我感谢我爸的是,他没有给我起个什么田卫红、田文革之类的名字。”
除了她对小时候北京门头沟生活的无比眷恋、出道时的困惑和迷茫,最让我忍俊不禁的是她给我讲了太多的早年“走穴”演出的故事:“‘走穴’除了各种闹剧就是要赶快结钱。不然演完了一找‘穴头’没了,得自己买车票。后来有一个原则——什么钱不带,回家的车票钱一定要带上。”
我至今仍希望能有人拍一部电视连续剧就叫《走穴》。
2023.5.27
 长三角微电影网
长三角微电影网